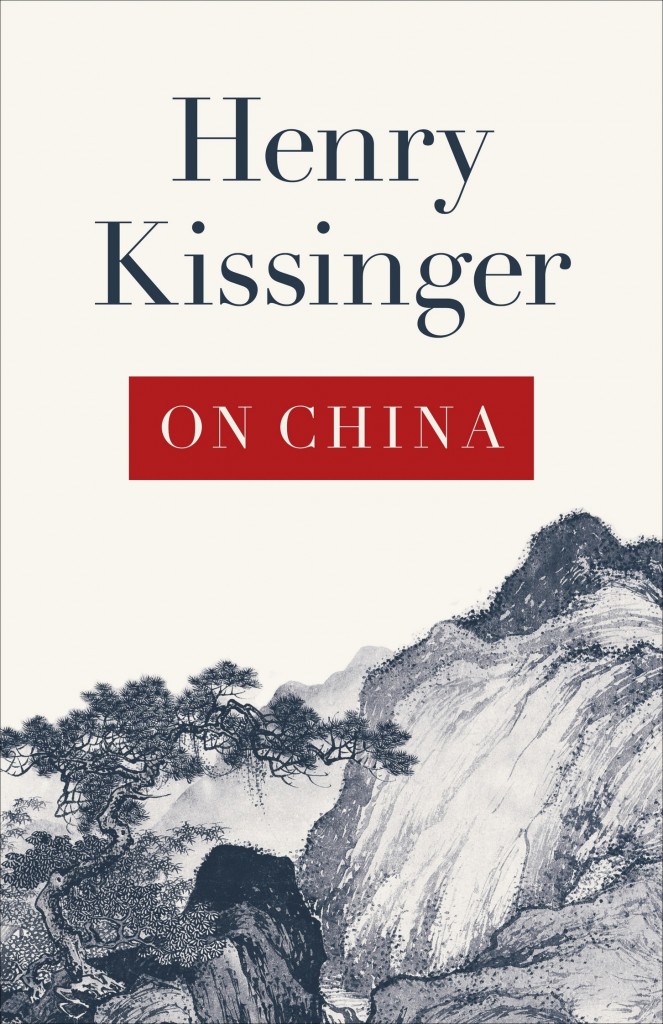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看基辛格的新书《On China》,觉得像是在看两本书:前半部是中国历史纵论,从中华文明的兴起、鼎盛、衰落、封建王朝的覆灭,儒家思想对统治与外交的影响,一直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周旋;基辛格本人则要到200多页之后才登场,这之后是他个人的亲身经历,以及对40多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见证与展望。
中美建交这段历史太富有戏剧性,即使已有大量公开史料,基辛格作为其中的关键人物,其亲述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恢复,这是冷战时期改变世界格局的大胆举动,而在这之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其情节更如间谍片一般。基辛格的回忆自然有许多外人不知的细节,但是更有价值的,其实是他对1960-197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分析,回顾当时东西方你死我活般意识形态上的对峙,是如何逐渐让位给地缘政治的权衡,过去的敌人如何成为盟友。
在中美恢复接触的历史上,“乒乓外交”往往被渲染成为神秘的起点。其实在这之前,中美政府高层之间已经建立了秘密联系。根据基辛格的叙述,“乒乓外交”发生时,他正在白宫拿着周恩来送来的手写英文信件,等待着来自中国的下一个讯息。
中美之间从对手变成盟友,双方都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当时中苏已经交恶,发生了多次边境摩擦,苏联在中苏边境屯有重兵,摆出随时开战,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的姿态。正当中国寻求改变战略格局之际,美国国内也出现了中国被美国“击垮”不利于美国利益的声音。
这种声音来自不同党派,尼克松的对手、民主党人肯尼迪在未当上总统前就曾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撰文指出美国的亚洲政策“可能过于僵硬”,1969年尼克松借用总统就职演讲的机会,以“没有任何国家的人民应该被孤立”向中国做出了暗示。上任之后,尼克松曾多次在政府内部表达欲与中国恢复关系的意愿,为外交政策的转变做准备,基辛格则试图与中国建立官方接触,尝试了波兰、法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等多个途径。虽然此时中国方面也在寻找接触机会,但因朝鲜战争之后的近20年间,中美之间不仅没有联系,而且充满敌意,两国之间的试探几乎成了捉迷藏。
书中的一个事件反映出当时中美两国之间鸡同鸭讲的状况。为了向美方传话,中共高层想到了美国记者、《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因此特别邀请他参加1970年国庆观礼,并安排刊登一幅在观礼台上斯诺站在毛泽东身边的照片,暗示斯诺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与此同时,斯诺被要求在海外发表一份他对毛泽东的采访稿,但必须在三个月之后才公开发表,中方的估计是,斯诺会先将采访稿送交美国政府,那么其中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访华的意思就非常明确了。但此时的斯诺因长期与中共接近,在美国早已被排斥在主流之外,本人都已移居欧洲,完全不受重视,也没有通往美国政府高层的渠道。基辛格带着遗憾地写道,中国方面的一番心机完全白费了。
等到斯诺的文章发表之时,中美高层间已通过第三国政府首脑建立了通讯渠道。1970年底至1971年初,基辛格从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个渠道分别收到了两封内容十分形似、以周恩来名义发出的手写英文信,明确邀请美国总统派人来北京商谈台湾问题。基辛格随即回信说可随时前往北京,强调愿意谈“任何问题”。
回信发出后3个月,没有任何回音。正在基辛格焦急等待之际,“乒乓外交”发生了。从基辛格的角度判断,他认为中国政府在借助“乒乓外交”打公关牌,把中美之间的谈判推向不可逆转的轨道。一旦尼克松临阵动摇,中国可以借美国国内渴望和平的情绪向美国政府施压,让他们不敢再背一次“让和平失去机会”的罪名。
这些当然是基辛格的猜测,作为外交官,基辛格不会去向周恩来问这个问题。中方至今似乎都没有权威的资料说明为什么周恩来在“乒乓外交”之后才回信同意基辛格访问北京。阅读本书的好处,是通过基辛格的叙述,把过去已经公开的事件从零碎和矛盾理得脉络清楚,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填补这些他所不知道的历史空白。
多少年来,基辛格从未离开过美国外交政策的圈子,尼克松和福特时期是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离开美国政府后依然从事外交政策咨询。美国外交圈中,他是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最多的人,从周恩来、毛泽东开始,到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有过深入的接触和敏锐的观察,但在书中他极少发表政治见解,大部分时候是在引述其他当事人的态度和立场。
这正是本书受到一些人批评的地方,有些评论者认为他一味欣赏中国领导人如何运筹帷幄,却没有对中国的外交内政做任何批评。这些评论其实并没有错,但是却批错了对象,我们不能忘了基辛格是一位职业外交官,不是一位政客或是政治活动家。他在观察评论他人之时,基本上都是以其外交手腕、谈判技巧、审时度势获取最大利益的能力作为标准。对于美国政治活动中的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他的看法是理想主义者必须认识到“理念的实现需要时间,因根据形势做出调整” ;而现实主义者必须理解“价值观的实际意义,并将之融入实际操作中”。
他对中国领导人的评价也是采用同样的标准,凭着他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验,基辛格从不相信他们的外交作风、谈判手腕是来自于意识形态,他相信这些共产党人其实都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考虑问题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和他一样深信地缘政治,在意识形态僵硬的外表下却是灵活的外交方针。
除了周恩来和毛泽东,他还特别欣赏邓小平的实用、江泽民的灵活,认为这两人都在审时度势、把中国带出备受孤立的国际环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于美国政客,他称赞了里根和老布什。里根对台湾有很浓的私人感情,但上台之后并没有把中美关系引向歧路而老布什更是在1989年7月违反自己刚刚发出的外交禁令,派代表秘密访问北京意图恢复外交对话。
基辛格试图用儒家文化的投桃报李、围棋中的“气”与“势”的概念,用“远交近攻”、“空城计”等等来解释中国领导人的外交艺术,有时候未免让人觉得有过度诠释之嫌。不过他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世界观如何影响中国的外交方针上,确实有不少敏锐的观察和精当的剖析。当谈到中国近代在外交上的节节败退之时,他对中国的外交官给予了深切地同情。
基辛格认为,现代的“外交”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新的概念。中国一向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这一方面导致中国缺乏对外扩张的欲望,因为在中华疆土之外、或者是茫茫大海的彼岸,无非都是“蛮夷之地”,没有必要去征服。另一方面,历史上中国遭遇的外族“蛮夷”们,不管初期如何强大,最终都会被中华文明征服,即使是凭武力占据中原的,最终都接受了中国文化。也就是说,外族的最大目标,其实是把自己变成中国人,甚至不惜抛弃了自己原有的文化。然而十九世纪清朝面对的来自西洋的敌人,不仅在科技实力上已经超过自己,而且这些新的“蛮夷”并不想成为中国人。这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是中国的皇公大臣们无法理解的。
中国的外交官们就在这种境况下被推上了前线,基辛格写道,依靠这些外交官的分析能力和外交技巧,以连哄带骗、层层退让、“以夷制夷”,为中国争取了时间。
基辛格特别提到的是李鸿章,他忍辱负重地多次代表清廷在洋人面前周旋,有时候甚至要以自己的血肉来达成外交上的妥协。可惜的是,中国并没有抓紧有限的时间增强自己的实力,因为大部份掌权者并没有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中国的实力地位一无所知,在对外政策上常常走极端,在极度强硬与全盘认输之间摇摆,浪费了时间,牺牲了国力,丧失了疆土。
延伸到现代,基辛格认为,新中国虽然在朝鲜战争上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因此确立了地区性的军事地位,不再需要听命于苏联,为自己赢得了独立的外交空间。中共领导人因此可以在冷战时期采取“远交近攻”这些源于传统文化的战略思想,与当时美国领导人的地缘政治考虑不谋而合,终于两国领导人都能抛开意识形态的束缚,一起走出了战略性的一步。
在《On China》全书中,基辛格一直试图在现实外交的背后寻找历史文化的根源,所以不难理解当他在展望中美关系的前景时,依然是回到历史中去寻找线索。他用的例子是1907年英国外交官克罗(Crowe)在德国统一时写给外交大臣的秘密文件《克罗备忘录》,声称英国与德国必有一战。基辛格对美国领导人的告诫是,如果你把“与中国一战”看成不可避免,那么所有中美之间的纷争都可能被看作是这场战争到来前的信号,长此以往中国真的可能变成美国的敌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这话是对美国人说的,其实同样适用于中国。而中美之间必须找到的,是一种“共同进化”的方式,彼此追求实现各自对内的使命,双方尽可能合作,并随时调整外交关系以减少冲突。基辛格本人,可以说一直是这一理念的积极实践者。

